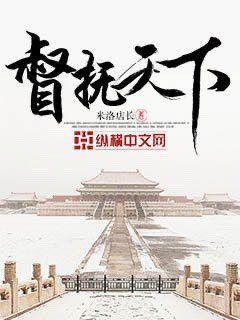“当然安全了,洋人那是大船,哪能进这里的水道呢?运河水道距离这里又远,官道在扬州西边,所以先祖确是聪明,离乱之世,隐居于此,是最好的办法。以后……”阮元看着一旁北湖风景,确是有些世外桃源之感,一时间自也惬意。可就在这时,忽听得脚步匆匆,原来是袁三从一旁奔了过来。
“老爷,不好了!”袁三刚刚看到阮元,便即上气不接下气地向阮元道:“扬州那边来的人说,几日之前,镇江……镇江已经失守了!”
“你说什么!”阮元听闻镇江失陷,自也吃了一惊。
“老爷,听说如今洋人兵船,已经布满了镇江江面,扬州城里面,都已经准备戒严了!可是,刘宜人和四公子他们……”袁三想到扬州城中的阮家家眷,却也担忧不止。
“唉……没办法了。袁三,咱们……咱们这就回去吧。”不想阮元听了袁三之言,当即便做出了南归的决定。
“老大人,这使不得啊?您方才……方才不还说离乱之时,只有这北湖才是……才是最好的避乱之所吗?”一旁那老农听着阮元竟然决定回到扬州,也当即劝阻道。
“我不能只顾着我一个人的性命啊?”阮元也向他苦笑道:“这次我来北湖,就只带了几个小孙儿,书之、孔厚、涧芳、恩海,他们都还在扬州呢。都是一家人,留下他们在扬州担惊受怕,我却一个人在北湖安享太平,这样的事,我……我不忍心啊?”
“老爷,可扬州一旦戒严,咱们不还是……”袁三也不愿阮元在这个时候回到扬州冒险。
“无妨,我之前便有耳闻,麟总河为了加强扬州防务,也已经准备从清江浦南下,来扬州赴援了。到时候我们就去找麟总河,让他带着我们回去,不就安全了?”阮元见袁三忧心不已,也只得宽慰他道:“我看啊,按洋人以前攻城的情况,他们就算破了镇江,一时间也不会再行动兵,若是扬州真待不下去了,咱们就一起再回北湖。可如今……如今总不能让书之和孔厚他们……他们就这样留在扬州啊?我身为一家之长,难道就这样看着家人身陷险境,却对他们不闻不问吗?”
“这……唉……”无奈之下,袁三也只得同意了阮元回归之议。果然,两日之后,阮元便即在城外与麟庆会合,一并回到了扬州,主持城防之事。
就在阮元决意南下的同时,京城之中,一场有关中英战事终局的讨论,已经进入了白热化阶段。
“皇上,奴才看如今英吉利人所提条款,若是能以此停战,则实为国家之大幸、天下之大幸啊。”这是穆彰阿的声音:“英吉利人这其余诸条,不过是开港、通商、赔偿军费之事,若是只拿这些钱就可以让洋人退兵,那比起各路大军前线的开支用度,已然少了一大半了。其中之难不过是这香港岛一节,可奴才听闻,那香港岛之上不过一二渔村,全岛不过方圆十里,并无可惜之处。若是能够以这样的代价结束此役,则皇上幸甚,江南万民幸甚啊!”
“皇上,如今即便是与英吉利人议和,这割让香港一节,亦是万万不可!”王鼎当即向道光反驳道:“国家版图,为国家之根本,尺寸不可与人!虽然那香港岛不过一隅之地,但也是我大清的疆土,那一两个村子的百姓,也是我大清的子民啊!若是果然向英吉利人割让香港,那天下百姓会如何看待皇上,他们不过是棋子,只要皇上和朝廷想放弃他们,就可以放弃他们吗?英吉利人又会怎么想,今日所得是香港一岛,那明日呢,后日呢?他们还会索要下一个、下两个,甚至下一百个香港岛啊!到了那个时候,难道皇上还要再行议和,再把那些岛屿也割让给英吉利人吗?!”
这时镇江战败的消息也已经传到了皇宫之中,事实上,早在英军攻破吴淞,进入长江之时,道光便已清楚前线战事几无胜算,开始筹划议和事宜。镇江一破,漕运断绝,道光更加清楚此战已然无力回天。是以这时朝堂之中,最主要的争议已然不在于战和,而在于如何应对英国提出的和谈条件。而令诸多大臣无论如何都不愿接受的,便是英国已经更改了议和要求,将索取土地扩大到了香港全岛,针对这个问题,穆彰阿与王鼎又展开了一轮激辩。
“皇上,如今形势紧迫,更何况前线大军,一年来几无胜绩,这不是很明显吗,至少一年半载之内,咱们不是英吉利人的对手了。那既然如此,咱们忍一时之辱,以求东山再起,这有何不可呢?难道如今文武百官之中,还有将略之才远胜于奕山、奕经二位大人,竟能力挽狂澜,在战场上反败为胜之人吗?”穆彰阿又向道光言道。
“皇上,臣以为,如今林则徐还在浙江,若是皇上决意一战,可再次起复林则徐,令其督师与英吉利人相抗。林则徐在广州多有整军备战之举,面对英吉利人,总不至于再吃了不谙敌情的亏啊?”潘世恩也在一旁向道光奏道,这时经过几年变化,军机处除了穆彰阿、潘世恩、王鼎三名宰相之外,赛尚阿复归军机处,道光也将祁隽藻、何汝霖二人补为军机大臣。因赛尚阿出外办理天津海防之故,军机大臣在京者共有五人,听潘世恩提到林则徐之名,祁隽藻和何汝霖也当即附议,请求道光重新重用林则徐。
“皇上,如今形势,即便重用林则徐,又有何用呢?”然而,身为领班军机大臣的穆彰阿,却依然不同意三人之议,继续向道光道:“林则徐这一年来,一直在闽浙沿海主持海防,一样收效甚微,又有谁能保证,林则徐上阵督师,便一定能反败为胜啊?更何况如今漕运已绝,英吉利人船炮坚利,就算咱们想要重整旗鼓,也是远水不敌近火啊?如今最好的办法,就是先认下和议,待洋人退兵,咱们再重整旗鼓,为时未晚啊?”
“穆彰阿,你个奸佞小人,大清有你这等奸臣做首辅,只怕……只怕已然衰亡无日了!”王鼎眼见穆彰阿一味主和,而道光神色游移,虽有不忍之色,却已然渐渐被穆彰阿说动,盛怒之下,再也顾不得同僚之谊,当即向穆彰阿怒斥道:“当年林则徐在广州整顿船炮,已然卓有成效,你为何竟然向皇上进谗言,要求罢黜了他?如今看来,海疆之事又是如何?琦善、奕山、奕经,一个个庸碌之辈,把大清的颜面都丢尽了!海疆自撤藩篱,使洋人肆意妄为,你穆彰阿就是罪魁祸首!你口口声声说什么重整旗鼓,那你这两年来作了什么?我凭什么相信你议和之后,还能重整旗鼓,而不是苟且偷安!你视大清威仪如无物,任凭洋人在案桌上出言宰割,日后海外各国,只会以为我大清软弱可欺,进而和英吉利一样,肆意侵凌我大清疆土!到了那个时候,你是不是还要说什么认下和议,还要说什么为时未晚?难道真要等到大清覆亡那一日,你才知道后悔吗?!”
“王鼎啊,你……你何必如此激动呢?”道光听着王鼎痛斥穆彰阿,心中自然清楚,被骂的表面上是穆彰阿,其实正是自己。无奈之下,也只好向王鼎劝道:“这两年的局势你也该清楚啊,去年开封大水,一半的开封城被淹了,你先前去治水不也花了半年工夫吗?去年除了英吉利人,湖广尚有聂人杰作乱之事,这你也应该清楚啊?前日户部统算军费,两年来开支已有两千余万之数,国库如今……如今已经没有足够的钱粮再来应战,甚至若是今年再有灾荒,朝廷赈灾的钱都要没了。如今这个局势,你说……你说咱们还打得下去吗?”
“皇上,即便议和,也绝不可答应英吉利人那割岛之议啊!”王鼎继续向道光劝道。
“皇上,王中堂说得没错,这国家版图之事,你不应该轻易言弃啊?”不想这时太后听闻道光意图放弃香港,也从寝宫特意赶到了勤政殿中,见了道光,太后便即言道:“皇上,老身年纪也大了,本来朝廷政事,老身是不该过问的,这二十二年,老身也从未来过勤政殿一次。可如今已不是寻常的外廷议政之事,这议和一事,事关朝廷社稷,事关大清的根本啊?皇上,国家疆土,尺寸不可与人,这个道理你应该清楚啊?国朝开国至今二百余年,从太祖高皇帝起兵,到高宗纯皇帝一统回疆,前后六世筚路蓝缕,方有今日之版图,凡一尺一寸之山泽水土,俱是历代先祖艰难开拓,你身为后世子孙,怎能仅因一战失利,便即擅许国土与他人呢?”
“额娘,儿臣也是没办法啊!”道光这时已是六十一岁高龄,可这时听到太后质问割让香港一事,心中难过,竟从龙椅上走了下来,跪在太后面前哭道:“两年了,朝廷大军在前线屡战屡败,几乎无一胜绩,洋人船炮实在胜过我们太多,这军器上的差距,不是我们一两年就能弥补得了的啊?如今国库也已经没了余钱,这仗再打下去,只怕……只怕是要天下大乱了,儿臣行此下策,也是为了……为了忍一时之辱,以求日后东山再起啊?”
“皇上啊,外人常言二百年来,我八旗战无不胜,可你仔细想想,即便是八旗,果然能够每战必胜吗?其实不是啊?”太后也向道光劝道:“圣祖皇帝驱准保藏,额伦特兵败青海,几至全军覆没,世宗皇帝和通泊一役,亦是损失惨重,高宗皇帝派兵入伊犁,阿睦尔撒纳突然作乱,伊犁守军亦是全军覆没,所以说几位先帝也都打过败仗啊?可几位先帝哪一个不是折而不挠,哪一个不是败而后战,他们哪一位曾经轻易言和,即便言和,又有哪一位放弃过前线将士已经打下过的疆土呢?皇上,如今或许我们船炮确实不如人,可大清尚有精兵数十万,江浙百姓大多也是同仇敌忾,即便言和,也不可在洋人面前有畏惧之态,更不可将社稷根本拱手让人啊?”
“额娘,议和之事,儿臣自有计议,额娘还是先回去吧。”道光又向太后劝道。
“皇上,臣还是那句话,可议和,但绝不可割地!若是洋人执意索要香港岛,那便不要与之言和!皇上,社稷根本之事,皇上若是开了先例,只怕皇上后世子孙,亦将悔之无及啊!”王鼎眼见道光心意渐决,只恐太后相劝亦自无用,也再一次向道光哭诉道。
“王鼎啊,你……你也累了,就先下去歇息吧。朕也知道,你操持河工有大半年了,这些日子已然疲乏,朕准你休沐一月,待你身体好了,再回军机处办事如何?”道光这时已然渐渐定下求和之议,又清楚除穆彰阿外,四名军机大臣中反对之声最烈者便是王鼎,无奈之下,只得将他支开。便即向门外道:“左右侍卫,王鼎尽忠国事,朕甚嘉焉,念其忧劳神瘁,着给假一月,你们……你们就先把王大人带回去吧。”
很快殿外几名侍卫便即上前,扶了王鼎向圆明园外而去。
“皇上,不可轻易言和,更不可割地啊!”王鼎虽被架走,呼喊之声却久久不绝,殿内各人亦自不住听得王鼎声音,直到门外几人渐行渐远,勤政殿之前犹有一二回响。
王鼎是陕西蒲城人,与乾隆末年的宰相王杰既是同乡,也有同姓之谊,无独有偶,王鼎却也继承了昔年王杰一身刚正不阿之气。如今眼见穆彰阿得势,道光即将同意求和,自己却被道光以“休沐”之名弃置在家,愤恨之下,王鼎只觉自己身为宰辅,不能匡正道光之过,便是莫大的耻辱。绝望之间,王鼎却也想出了一个最为激进,也最为决绝的办法——用自己的性命,再向道光进谏一次。
“皇上,臣老了,臣实在没有能力再改变什么了。可即便如此,臣不希望后世子孙,竟要永受国耻,竟要眼睁睁看着江山社稷残缺之状啊?皇上,穆彰阿实乃奸臣,您绝不可信,香港之事,您也绝不能答应英吉利人的无礼要求。臣此次上疏,便为绝笔,就请皇上看在老臣这条命的份上,听一听老臣的肺腑之言吧!”
这日王鼎在家中屏退旁人,将自己关在书房之内,向道光写下最后一封遗折。奏折写完封好之后,王鼎便即在书房内投缳自尽,终年七十五岁。
然而,王鼎的书信却未能按时送到道光手中,早在王鼎自尽后不久,穆彰阿便得知了王家变故,并抢先派遣自己的亲信军机章京陈孚恩前往探视。结果陈孚恩先是假借道光之名,令王家隐瞒王鼎死因,又藏匿了王鼎遗折,另作伪折以答道光,对于王鼎之死,亦仅言暴病而卒。道光慨叹之下,也只是加赠王鼎太保之衔,赐谥号文恪,而王鼎“尸谏”之举,却并未获得任何效果。
早在镇江城破之前,道光便已授意前线的文武官员,准备议和事宜,并且将伊里布召回江宁,以备和议之用,而英军在攻占镇江之后,也只是将军舰向西开进了十余里,准备前往江宁订立和约。是以阮元回到扬州之后,虽有城中戒严之令,却也知道中英双方已然开始议和之事,先前的忧虑之心自然减轻了不少。但即便如此,阮元和麟庆却也不敢怠慢,每日仍是前往扬州城墙之上视察城防,因腿脚不便,每日阮元出行,便只用舆轿。
这日麟庆和阮元一道视察南城,居高临下,眼见数十里外便是镇江城楼,若是英军果然北进,自是一览无余,而眼前的扬州城墙之上,只有寥寥七八门大炮,俱是百年之前旧物,甚至不少砖石均已脱落,露出里面的野草。麟庆看着全然无力与英军相抗的城墙,也向阮元问道:“阮相国,英吉利人如今是……是要去江宁订立和议,不是要往扬州出兵,这……没错吧?”
“麟总河,咱们防得不也就是个万一嘛?”阮元也苦笑道。
“唉,话虽如此,可你看这扬州城墙,这……这怎么守城啊?”麟庆也向阮元叹道:“这里少说也有一百多年不打仗了,城防、军械,根本不堪使用啊?镇江那可是三千人的旗营,如今都败了,我麾下不过五百河标,从来就没打过仗,我知道你们也练了一些乡勇,可这枪炮军械都不够啊?相国那句话说得是……尽节成仁,罢了,若是洋人真的前来攻夺扬州,我率众死战,然后自尽便是,前人做得,我有什么做不得的呢?只是阮相国,您一家老小我看着……您那些孙儿也都是读书的好材料,留得青山在,不怕没柴烧嘛?不如再过几日,待相国家里收拾得当,我遣人送你们一家回北湖,你们就……就不要留在这危城之中了。”
麟庆所言“尽节成仁”,乃是阮元致仕后拜谒史可法祠时所书,此时麟庆之言,便是既然道光已经让他协防扬州,那自己也只有与城池共存亡一条路了。阮元听着麟庆之语,自也慨叹,但阮元也清楚自己一家即便留在扬州,对于守城之事也帮不了多少忙。只得向麟庆笑道:“既然如此,也多劳烦麟总河了。”
“总河大人,总河大人,不好了!”不想就在这时,一名河标兵士匆匆而上,见了麟庆,当即拜道:“总河大人,瓜洲那边传来消息,说……说有五艘从湖广前来扬州贩运粮米的粮船,在镇江江面被英吉利人的船扣下了!这……这可如何是好啊?”
“你说什么?!这……扬州城从来人口稠密,存粮不多,尤其是如今七月时节,粮铺全要靠四川湖广的米粮接济,这些粮船被洋人扣下,那用不了几日,扬州就要断粮了啊?这……扬州如今还有许多百姓呢,可如何是好啊?”麟庆做南河总督已有多年,自然清楚扬州民情,深知一旦数日之内粮船不能及时到扬,只怕用不着英军进犯,扬州百姓很快就会因为乏食陷入恐慌。届时一旦出现民变,百姓又迟迟看不到粮米,那局势可就不是自己能够控制的了。
“麟总河,要不您让我去吧。”不想这时竟是阮元主动提出了前往取船的建议:“我和英吉利人在广州的时候就多有交涉,和他们打交道,如今扬州城里,还有比我更合适的人吗?”
“阮相国,这怎么使得呢?”麟庆听了阮元主动请缨,也当即劝阻道:“您这都快八十了,腿脚也不方便,哪能劳您走这一趟呢?再说了,英吉利那边,若是眼见有个大清旧日宰相前去议事,那他们会怎么想?他们巴不得把您软禁起来,然后对朝廷漫天要价呢?所以我看……您还是不要去的好。”
“麟总河,我这不还有轿子嘛。”阮元也向麟庆笑道:“再说了,我不过是个致仕大学士,对朝廷而言,早就没什么用处了,洋人把我软禁起来?何必多此一举呢?朝廷不用,也不需要为了我一个致仕大学士,再多担什么心的。更何况,若是英吉利人真敢那么做,那……尽节成仁,这本就是我写给史阁部的,我又为什么不能……不能这样做呢?而且真有那样一日,英吉利人再想订立和约,只怕还要在道义上更吃亏一些吧?我知道,英吉利人从来对财利之事斤斤计较,不能帮他们达到最大利益的事,他们不会做的。”
“阮相国,这……唉,如今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?我……我帮您备船,再挑几个得力的下属,我尽力……尽力护您周全吧。”麟庆虽然不舍阮元前去敌营,可眼下却也别无他法,无奈之下,只得答允了阮元的要求。
随后麟庆便即派了几名兵士,扮作侍仆,同阮元一并乘船南下。船行一日,便即到了瓜洲。停泊瓜洲之际,一行人又听闻英军将帅为了议定和约,大半皆已前往江宁城外的静海寺。想着只有见到英军之中身份颇高之人,方能言及还船之事,阮元也只得告知几名兵士继续开船,次日下午,便即抵达静海寺之畔。
通报过一行人来历之后,阮元却也在静海寺见到了一位故人。
“莘……莘农?”
“伯元?你……你怎么会来到这里呢?”原来这时听闻阮元到访,主动前来迎接的清朝官员,正是被道光起复前往江宁,准备同英军商议和约之事的伊里布。此时另一位大臣耆英尚在路上,是以静海寺事宜便一律由伊里布统辖。然而伊里布见了阮元,言语却既是惊讶,又是不忍,连忙向阮元道:“伯元,这地方你不该来啊?咱们来这里是迫不得已,只能和洋人签约了,以后……以后还不知外人要怎么看我和耆英大人呢。伯元,你又何必在这个节骨眼上来趟这趟浑水呢?”
“莘农啊,我……我本来也不想走这一趟啊?”阮元听了伊里布之言,却也只得苦笑道:“可如今这场仗,火都快烧到扬州了,扬州的米船又被洋人扣下,若是我不走这一趟,扬州百姓怎么办呢?不过莘农也自放心,洋人只要能把米船还给我们,我明日便走,总是……总是不能让你们再担心我了。”
“洋人还你们米船?伯元,这……这能成吗?再说了,你是太子太保,以前做过大学士,若是有你这样的贵人来静海寺同洋人谈判,那洋人把你软禁了可怎么办?我……我手下也不过十几名侍从,没有……没有兵可用啊?”伊里布还是颇为忧心地向阮元道。
“莘农,洋人软禁我做什么呢?洋人要的是议和,又何必多生事端啊?”阮元也向伊里布安慰道,这时伊里布身旁的一名侍从也走上前来,向阮元和伊里布拜道:“老爷、阮太保,小人已经向英吉利人那边送了帖子,英吉利人那边有个头目,说……说可能认识阮太保,想着……想着请阮太保过去一见。”
“英吉利人认识……认识我?”阮元听着那侍从之言,自也好奇,只得心中定下,先见那英国人一面,再作定夺。想到这里,阮元便也请那侍从在前引路,身后跟了两名麟庆派来的兵士,以防不测。那静海寺中此时已然空出了几座房舍,以备数日后和谈之用,房舍左右各自站立着几名清军兵士与英军步兵,阮元也在那侍从引领之下,走到了一座小舍门前。只见小舍之中,果然已坐了一名英国老者。老者眼见阮元到来,便也向一行人问道:
“这位老先生,您可是……光禄大夫、太子太保、予告大学士阮元阮先生?”那“予告”一词与致仕同义,予告大学士即是致仕大学士。而真正让阮元感到惊异的是,这人竟然说得都是流利的中文。
“老夫正是阮元,你……是你?!”这间房舍门户向西,此时已是未初时分,日光自西向东而照,正将那老者样貌照得清楚,虽然距离先前会面之事,已经过了二十余年,但阮元一生所见英国之人并不算多,这一次自然看得分明。眼前之人,正是五十年前随马戛尔尼使团前来中国,二十六年之前又作为阿美士德副使出使北京的小斯当东。不觉五十年时间过去,当年马戛尔尼使团中的那个少年,此时也已经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。
“没想到啊,阮先生,我来中国内地三次,居然见了您三次啊?”小斯当东也不禁感叹道:“只是阮先生,您……您为何会出现在这南京城下呢?”
“我是江北扬州之人,如今已然致仕在家,这场仗……本来我也是不愿参与的,但没办法,你们的兵士如今在长江之上扣下了前往扬州的几艘米船。我想着既然你们也已经同意和谈,那这个时候你们还在对长江上的米船动手,是什么意思呢?使者先生,我想听您一个解释。还有,您又是为何会出现在这里的呢?”阮元见了小斯当东,心中虽多有感慨,可回想起粮船被扣,尚不得还,言语之间却是平淡如水,并无半点客气之处。
“阮先生,我……我是特意同国内外相商议之后,去年年末决定来中国的,您应该清楚,这场仗,中国已经败了。可你们……若是五十年前你们的大皇帝能够同意马戛尔尼爵士的要求,你们又何必打这一仗呢?五十年前的人,除了我都不在了,所以……我想着再来中国一趟,帮我父亲,帮马戛尔尼爵士见证他们的遗愿完成的那一刻。我想……看着你们签下当年就应该定下的条约。”小斯当东一边说着,也一边向身旁几名兵士问了几句,兵士当即退下。过不多时,便又返回,向小斯当东耳语了片刻。
“阮先生,这件事是我们疏忽了,方才我遣他问过了司令,司令说,不是他的意思。”小斯当东也向阮元解释道:“司令到了镇江之后,一向严明军纪,不许劫掠百姓,您家乡的米船被扣下,应该是那些不听话的印度兵士擅作主张。如今司令已经下了军令,告知镇江那边驻军,让他们把米船还给你们,阮先生回到镇江江面,自然就可以把米船接回去了。”